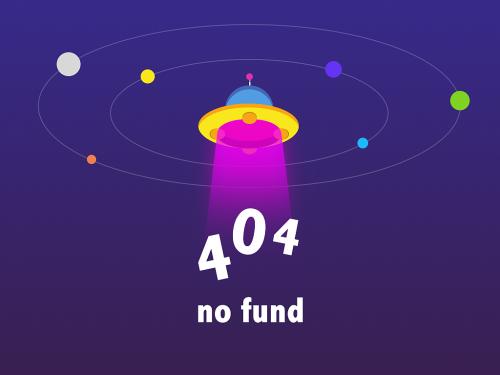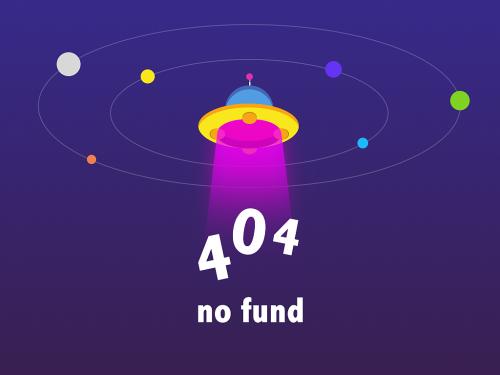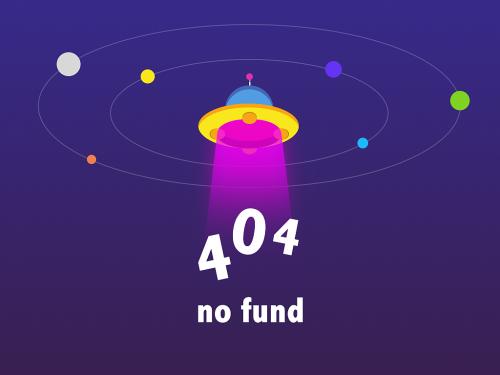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:: 最后的牵挂-威尼斯2299
她留下的照片不多,关于她,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张温馨动人的合影:年轻秀美的母亲平静地坐在藤椅上,轻托着一位孩子的小手,透出淡淡的祥和——如同这世间每一对幸福的母子,整个画面弥漫着暖人身心的甜蜜氛围。
照片中稚气可爱的孩子名叫宁儿,那时他才一岁零三个月。宁儿不会想到,这张照片是他和母亲骨肉分离前的最后合影。从此,母子生死两茫茫,一别成永诀。二十年后,他终于收到了母亲留给他的最后家书:
“宁儿,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,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,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!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。希望你,宁儿啊!赶快成人,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。”
宁儿的母亲名叫李坤泰。另外,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化名——赵一曼。
今天,重新走近赵一曼,我依然很难把这位清秀美丽的川妹子,同那位红枪白马的女英雄联系起来。在无数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中,赵一曼的身份总给人以强烈的反差:她是柔肠百结的母亲,又是驰骋沙场的战士;她是重伤被俘的弱女子,又是钢筋铁骨的革命者……
从1935年11月受伤被捕,到1936年8月英勇牺牲,这短短九个月,是赵一曼人生中最悲壮英勇的九个月。直到今天,但凡见过赵一曼女士照片的人,都很难想象如此一位清秀柔弱的四川女子,到底如何挺过了敌人那些闻所未闻的酷刑?
从最开始的汽油灌、皮鞭抽、烙铁烫,加码为扎铁签、剥肋骨,甚至动用残忍的“秘密武器”——电刑,日本人对赵一曼的刑讯折磨不断升级,用尽了各种酷刑。直到今天,阅读那些赵一曼被日寇刑讯的档案记录,依旧令人压抑痛苦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即便已经遍体鳞伤,赵一曼仍展现出一种令敌人胆寒的力量。连审讯她的日本人大野泰治也被吓住了:“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,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,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。”
接连几天的审问,大野泰治毫无所得,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,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,用鞭梢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……赵一曼疼痛难忍,昏迷过去好几次,敌人以为这下该开口了。不料,醒来后赵一曼义正词严地控诉:“我是中国人,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,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……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,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?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,别无出路。”
后来坐在战犯席的大野泰治供述道:“她那种激愤之情,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。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,但讲得有条有理,使人一听就懂……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。”
但在当时,日本人的报告中对此百思不得其解,在对赵一曼施加长时间高强度的电刑后,“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,确属罕见,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”。
1935年末,因赵一曼腿部的伤口溃烂严重,已危及生命,敌人便将她转移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外科一病区进行监视治疗,由伪警察24小时看守。
一个叫董宪勋的新警察负责看守赵一曼,不久敌人又派来一个17岁的见习女护士韩勇义。赵一曼通过观察发现,这两个年轻人尽管暂时屈身于敌人的统治之下,但都有着一颗爱国心。只要爱国,就是自己的同胞;而对同胞最好的爱,就是真诚的感召。她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爱护着他们,经常给他们讲抗日故事。这些故事如同阳光,散发温暖、驱除黑暗。最终,董宪勋和韩勇义下定决心:不再委身敌巢,要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、走向光明。
韩勇义帮赵一曼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三区,那里是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方。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,得钱60元充作经费。董宪勋则找人做了一顶小轿,用来抬赵一曼。
他们在1936年6月28日晚上的一场大雨中,成功把赵一曼从医院背了出来。三人先是乘着雇来的小汽车,然后又把伤重不能行走的赵一曼转入轿子,最后轮流背着她,一路逃向抗联的游击区。
然而,就在距离日伪最后封锁线只有20公里的时候,他们被敌人追上了,赵一曼再次落入敌手。
这次营救行动虽然功败垂成,却给敌人以极大震撼。他们对赵一曼进行革命宣传的能力非常惊叹,竟对照反省起自己阵营的不足来:“回顾赵一曼等逃走的事件,使我们要加以考虑的是:关于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宣传工作,以前实在是有只讲理论或流于形式,因而有改进的必要……”
实际上,赵一曼随机应变地欺骗了敌人,一直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。她态度坦然地编造情况,从容应对敌人的审问。即使生命的最后一刻,她在遗书中也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叫李坤泰,而是延续了在审讯中编造的口供。她细心地虚构口供是为了保护抗联组织,也是防止敌人对亲人的追捕和迫害……
赵一曼总习惯把所有苦难一肩挑起来。和她一同被捕的还有一名抗联战士,16岁的杨桂兰。赵一曼不愿让她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受敌人的折磨,她暗中叮嘱杨桂兰编造假口供,就说是来伺候赵一曼养伤的,其他一切都不知道。由于赵一曼千方百计地保护,小杨被敌人关押了二十八天后,得以释放回家。
而在第二次被捕后,赵一曼又把越狱的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,一口咬定是自己用重金贿赂了董宪勋和韩勇义。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,施电刑,上大挂,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,问她为什么帮助赵一曼逃跑。她坚定地说:“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、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……”最终因赵一曼的竭力开脱,韩勇义被判四个月徒刑,最后释放出狱。这位勇敢的女性虽然被酷刑摧垮了身体,后来年仅29岁就病逝,但她自始至终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
费尽心机的日寇最终意识到,他们对赵一曼施加的种种酷刑都是徒劳。敌人终于绝望,他们决定将赵一曼押回珠河,要用她的鲜血恐吓当地抗日群众。
直到她最后牺牲,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,审讯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“湄州人”。日本人不会明白,在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,小孩遇到倒霉事,会自嘲“走湄州”了。受尽酷刑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嘲弄轻松的玩笑,回击了日本人。
1936年8月2日凌晨,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。生命最后的时刻来临,赵一曼更加从容镇定。这个世上,儿子是她最后的牵挂。从哈尔滨乘火车押往珠河的途中,赵一曼从看守那儿要来纸和笔,在晃动得很厉害的车厢里,开始一笔一画写下那封给儿子最后的遗书……
这舐犊情深的母爱遗书,这牵肠挂肚的最后叮嘱,是泣血深沉的人间至爱,更是寄望来者的殷殷重托。今天,这封感人肺腑的红色家书早已家喻户晓,深入人心,回响在赵一曼浴血战斗过的白山黑水,回响在神州大地的琅琅书声中,激荡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,焕发出一个民族英勇奋斗的力量……